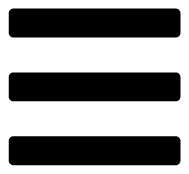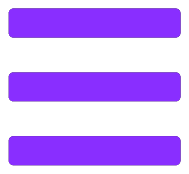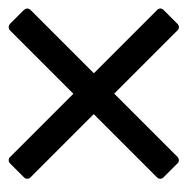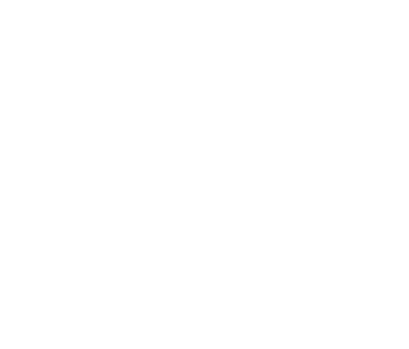前言

X 美术馆三年展是一个持续性的探索项目,试图通过视觉艺术和参与了人文进程发展的其它领域来共同探讨千禧时代思潮。三年展关注新兴青年艺术家,将以三年为期对中国当代艺术及其发展进行节律性回顾。
距今100年前,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广播电台KDKA在1920年初冬开始了第一次美国总统大选的广播。实时媒体与政治事件的结合所引起的巨大冲击标志着大众传媒新时代的开始。
此后,实时媒体及其即时性大大提高了信息共享的效率,并进一步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即时的特质与亚里士多德对友谊和“共感(con-senting‘synaisthanomenoi, 共同感知’)”的阐述相呼应,他说:“一个人同时需要‘共感’其朋友的存在,即共同生活、分享类似的想法和行为会促发此种‘共感’的产生。”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关于共同感知的思想本质来思考当下社会的信息共享:区别于数字时代之前的单向信息输出,当今的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更多的实时交流和沉浸式交互体验,我们的共同感知和共时存在性也被前所未有的放大。从XR(扩展现实)、AI(人工智能)到最近开始广泛应用的5G技术,我们栖息的场域在不断被扩展,也不断挑战着我们感知事物、感受共存的方式。
电子屏幕和VR眼镜将信息时代的产物展现在我们眼前:DRM免费的视听产品、可以装进口袋的电子图书馆,人们可以通过沉浸式线上展览浏览名作和珍馐文物,各式各样的数码产品作为社会赋能者为徜徉在电子世界的人们导航……尽管如此,非物质的丰富和过剩的信息反而导致了物质匮乏,现在人们所寻求的可能不仅仅是一条完美的分割线,更是在自我和冗余的信息之间找到理想的距离。
当代艺术远离时间、流派、纪律的界限和二度诠释的束缚,通过这样的距离来对我们的时代进行精确的解读。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将这一距离理解为能够感知“黑暗”并看到其“朦胧”。在神经生理学中,黑暗是由“脱细胞”激活产生的特殊视觉效果,因此,黑暗不是空洞或看不见,而是由我们自己视网膜的特定细胞激活所引起的视觉感受。当代艺术家们是用一只眼睛来观察并感知世界的人,他们保持与光明和黑暗的距离,将知识和经验转化为有形或无形的表达。
对于千禧一代的艺术家们来说,自从他们对世界产生好奇伊始就被无处不在的即时媒体所环绕,他们目睹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借用科技之手来创作或审视如同他们的第二天性。当今时代人与技术的交融带来了很多便利以及惊喜时刻,但随之而来的也有恐惧和担忧。艺术家意将两者放置在天平的两端,借用作品来反映此种左右摇摆的状态,而非得出一个特定的结论。
关于展览
“How Do We Begin? “从我们栖于的当代生活出发,庆祝数字时代所蕴育出的知识与信息的开放性与便利性,以及新媒体和尖端技术所带来的全新感官体验和惊喜时刻。同时,正视毒性信息的入侵对我们现实关系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干预和扰乱。对个人而言,我们与家庭、群体和自我建立关系的方式一直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共感(con-senting‘ synaisthanomenoi,共同感知’)”。“共感”认可处于相同变化状态的重要性,进而指向集体记忆的建设和思维的趋同。
在以共享共生为明显特征的表象下,当代艺术跨越了学科的局限和知识的界限。此次展览将展览空间视为合作与生产的场所,期望激发和促进学术思想力之间的信息知识互换。
恰逢第一个实时大众媒体(商业广播电台)KDKA 诞生一百周年之际, “How Do We Begin?”邀请在艺术和人文科学发展进程中活跃着的当代艺术家以及其他学科的从业者们,对信息时代的多方面社会现象进行反馈与回应,并尝试通过感知、共享和共存来探究其意义。当今时代最前沿的技术和设备如同人体感觉器官的延伸,在放大我们感知能力和情感的同时,也将我们在这个非物质的世界中逐渐同步化,消除了地理上的界限。艺术家们将以当代社会诸多现象学事件作为出发点,借由多种艺术媒介和设计手法来思考当下并描绘未来。
“How Do We Begin?”试图提炼处于持续演变中的千禧时代思潮, 并且积极邀请、鼓励观众和艺术从业者们参与其中,共同探索并构建我们与时代的交互关系。
1. 科技与媒介

2020年标志着“Web 4.0”的开始,在这个全新的网络时代中,每个沟通和互动的层面上都将植入智能虚拟助手,它们会通过模仿人类的思维方式而逐渐进化演变。在这样的语境下,大数据和个人信息将成为一座连结虚拟与现实的桥梁,进而,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也将受到混淆。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于1964年提出过一个现今时代仍颇具前瞻性的论点:信使(courier)—即承载信息的媒介本身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感知,这与内容无关,媒介决定了意识。而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驳斥了麦克卢汉关于技术本身可以决定人类感知和社会变革的想法,认为社会生活和技术发展密不可分,内容将由媒介形式塑造。
相应地,本节中的艺术家将从两个角度探讨这个主题:一方面关注于媒介本身,关注人类如何与技术和设备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则关注新媒体所带来的内容生产,从社交媒体如何扰乱真实的人际互动到自我审查“制度”的建立。
2. 社会观察者

作为具有反精英主义精神的存在,流行文化在现象社会学中是无处不在且占有主导地位的。在波普艺术开始盛行的时代,艺术家们通过引用流行文化来创造煽动性的时刻和事件,进而对大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批判。
当代艺术家从流行文化的意象和物件中获取参考和灵感,从而对当下社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日常细节进行批判。这个由数字电路所控制的世界在催生了文化模因和网络语言的同时加速了这些信息的传播。具有网络意识,或许是与社交媒体对美学、文化和社会的强烈侵入性和解的最佳方式。
光纤连接着每个个体,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和补给品。我们已经难以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世界中,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甚至无法回到70年代以前。互联网的出现导致了人们对真理以及客观评判标准的丧失,人工智能深度学习(DeepMind)及其他尖端技术加剧了这个后真理时代中事实与另类事实之间迂回摇摆的现象。对于现代大都市的公民来说,暂时性地重返非数字科技世界反而被打造成冥想甚至自我净化的体验,那么现在将通过何种形式,我们能得以摆脱数字媒体的假肢,与精神灵性和肉体本身重新建立联系。
3. 作为叙事者的艺术家和建筑师

历史从不是单一的叙事,城市景观、建筑痕迹、建筑楼宇以及它们所特有的材质不带有偏见与预断地向大众讲述着一个地方的过去与现在。建筑师—物理上的叙事者们,早已偏离了在线性基柱上堆砌生活单元的工作方式,转向探索当代城市中技术发展如何与叙事性相交织的一系列命题、以及形态和物质性如何抵抗和干预虚拟化,并与其共存。
“定制”将不再是一种相对私人的高端营销手法,算法和机械自动化正在逐渐取代陈旧的建筑定制,建筑师们将以何种方式和地位存在于这个被算法和人工智能统治的世界中?或许我们可以从1923年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所提出的“居住的机器(machines for living)”中汲取灵感,在柯布西耶的语境中,“机器”被解读为‘装置(dispositif)’即可以在社会主体内部建立关系、 机制和知识结构的系统。 艺术家和建筑师是自我实现预言的装置(dispositif)的生产者,他们捕捉、定向和阐释生命、信念和话语。 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家和建筑师们极力保持着与反乌托邦之间的距离的同时,激发着我们对于周围建筑环境的思考。
About The Artists
About The Curators